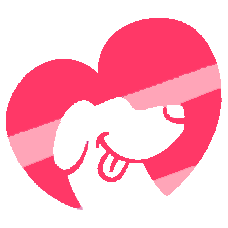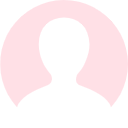出发不是为了逃离,而是要扩充自己当下的生活,让眼前变得不再苟且。
朋友圈里有一句哲理味的流行语:“这世界绝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。”乍看颇有道理,但经不住细想。地平线会随着人前进的脚步而不断远退。远方,就是永远达不到的地方。若把诗意寄托在永远达不到的地方,不论人走到哪里,都免不了眼前的苟且和琐碎。
“远方”和“眼前”不应是彼此对立的两极,而是心灵所映照的不同层面。不过立论若仅限于此,仍不免心灵鸡汤之嫌。哲学之用在于深化思考。就此问题,我想援引一个长期以来被标签化误读的伟大观点——明代哲人王阳明提出的“心外无物”。
《传习录》记载了一条讨论此观点的著名公案:“先生游南镇,一友指山中花树问曰:‘天下无心外之物。如此花树,在深山中自开自落,于我心亦何关?’先生曰:‘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。你来看此花时,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’”“心外无物”最容易引起的误解就是把心和物当作一种容器和里面装的东西。该朋友基于常识提出了质疑:山中花树(“物”)独立自存,可以跟“心”这种容器毫无关系。王阳明的回答是:只有在“看”的过程中,在“一时明白起来”的时候,心和物才同时存在,否则两者皆归于寂灭。这显然不是容器和内容物之间的关系。
“物”的存在有赖于人心,似乎最令人费解。王维有诗“木末芙蓉花,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,纷纷开且落”。山中花树自顾自地盛开和凋零,无待于观赏者。没有被任何一个人看到过、听说过、梦想过的事物太多了,难道它们都不存在吗?诚然,作为某种植物的生殖器官,它当然是在那里的,而作为“花”却不能算是存在。人的生活当中有了装点自身和环境、表达情意的需要,才有了我们熟悉的用于装饰、示爱、观赏的“花”的观念。在蜜蜂眼里的花树,也许是这种小昆虫的家,也许是它的宴会厅。这当然是比喻的说法。“家”“宴会厅”这些观念也是专属于人的。对于动物来说,那可能只是一个激发某方面本能反应的刺激源而已。因此,“山中花树”是否存在并非与人心无关,花不在人心之外。
不唯花,万物皆如此。人所面对的全部宇宙,并没有什么是自己意义世界之外的东西。哪怕那些看似跟人完全无关的星球,当我们的探知或者想象达到那里的时候——不论这种探知是多么粗浅,想象是多么离奇——它就跟我们当下的生活发生了关联,已经是有意义的存在。“眼前”总会因为“远方”的存在而发生某些改变。
可见,“心外无物”之说的重点并不在“物”,而在“心”。王阳明说法的紧要处是:如果没有对于万物的“明白”,“心”也就“归于寂”。心物两寂,则顽冥如木石,无复为生灵。略有一丝光亮,也是蒙昧无明的动物状态。动物越是低等,就越局限在基本生存的范围内。在蜜蜂的世界里诚然有另一种面貌的花树,但蜜蜂恐怕不能像人一样去欣赏、去改变自己的食物。它的世界里更没有潺潺的流水、巍峨的高山,它可能连花树底下的草也看不见。与动物相比,人之为人的一个特点是心量广大,可以映照出广袤的天地,可以欣赏鸢飞鱼跃的美。因为能见万物,能望向远方,人心也变得廓大。
各个文明的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这种“唯心主义”的说法,都是要强调人的心灵空间。西方哲学家说“存在即被感知”,从认识论谈到信仰;印度宗教家的“万法唯心造”和中国人的“心外无物”则直指心性的修为。儒家思想常追问“人之异于禽兽者”,因为人会不自觉地放弃自己异于动物的特点。限于本能生活的人,不唯看不见远方山里的花树,就连天上的云、月亮和家门口的树、花草等等这些每天都在眼前的事物,也会视而不见。对亲人朋友悄然改变的容颜,也一样视而不见。正是太多的视而不见,人的生活才变得苟且,容易被引诱和驱使。庄子说,哀莫大于心死。哲学之于人生的价值之一,就是帮助人恢复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的眼光,去重新发现世界,发现自己的生活。
世界那么大,人还是要到远方去看看。但出发不是为了逃离,而是要扩充自己当下的生活,让眼前变得不再苟且。
【野兽情书】诗意不必在远方